摘要:在古代的名人中選一人做朋友,我只選擇蘇軾。
在古代的名人中選一人做朋友,我只選擇蘇軾。
作者/李舫
2000年千禧年伊始,法國巴黎,有一家報紙——《世界報》,它的主編叫作“讓-皮埃爾·朗日里耶”。他和他的同事們決定用一種創新的方式,迎接新千年的到來。
怎么慶祝呢?他們決定用專欄的形式,寫一批專欄文章,講述在公元1000年-2000年這一千年中生活的世界知名的重要人物的生活故事,覆蓋北美洲、拉丁美洲、歐洲、亞洲。
這家報紙用了六個月的時間,整理自公元1000年一直影響到公元2000年的重要人物的備選名單,這真是一份浩如煙海的名單,他們在這份名單里,整理出12位重要人物,并編輯成冊,名為“千年英雄”。這些文章于2000年7月份發表。

2000年法國《世界報》報道蘇東坡圖片來源:香港文匯網
中國的蘇軾(1037-1101)就是這些“千年英雄”中的一位,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國人。
蘇軾有一百余萬字的詩詞、雜記、隨筆、親筆題書和私人信函,以及大量的他同時代的朋友和學者評論他的隨筆、傳略。當然,蘇軾本人不寫日記,這不符合他的性格,蘇軾同時代的很多人都有寫日記的習慣,司馬光、王安石、劉摯、曾布等等,寫日記這事對他來說太有條理、太扭扭捏捏了。蘇東坡一生寫過數千首詩詞、八百余封私人信件。他寫過一本雜記,是他對各種思想、旅行、人物、事件的記載——沒有時間,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邏輯。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話,是寫給他的弟弟子由的,也是寫給他自己的:
吾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,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。
蘇軾,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(1037年),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(1101年),也就是華北被金人攻占,北宋滅亡前二十五年。

在他短短64歲的生命里,蘇軾由于其坦率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。在權力陰影下,他的政敵非常多。他既是各個陣營對抗的參與者,也是受害者。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,他的一生都是在動蕩中度過的,“大起大落”,就像“坐過山車一樣”。在他職業生涯中,他一共有30次委任,17次失寵或者被流放。今天他還是受人尊敬的高官,明天卻什么也不是,被人蔑視,并受到責罰。
蘇軾的命運在朝廷和皇帝的心情中搖擺不定。他行千里路,經歷過榮耀與不幸,擔任過太守,也曾經是階下囚,從中國的最西北到中國的最南端,從寒冷氣候帶到海南島的熱帶氣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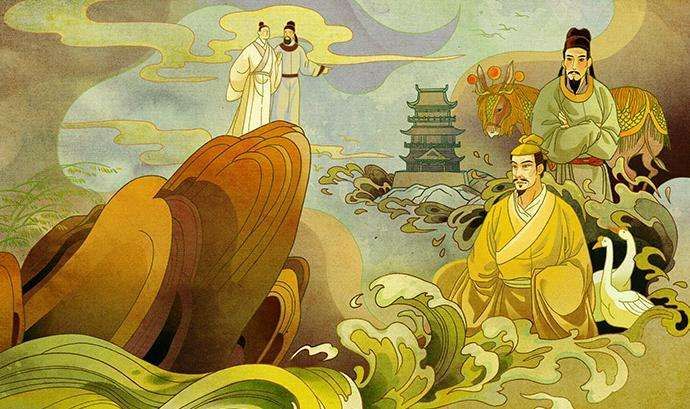
1079年,他甚至因為“欺君之罪”的罪名而坐牢130天。他走出御史臺監獄的時候,已經43歲,這一年,他被流放到黃州,即湖北的一個小城市,在那里他開始了新生活。
沒有職務,也沒有薪水,他成了農民,需要養家糊口。他找了一塊坡地開墾,這塊坡地被他稱為“東坡”。這就是蘇軾作為“蘇東坡”的來歷。在千年來的時光中,百姓更喜歡稱呼他“東坡居士”。
一、豪放
中國文化史上,李白是詩仙,杜甫是詩圣,只有蘇東坡被稱為文豪,他是古今第一文豪。
說到文豪,我們能想到誰呢?荷馬、但丁、歌德、莎士比亞、雨果、托爾斯泰、巴爾扎克、博爾赫斯。在中國,我們最先想到的,應該就是蘇東坡。
美國西華盛頓大學東亞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唐凱琳說:“接觸了蘇東坡的文章之后,我被他的那種自由自在、想象豐富的思想所吸引。”唐凱琳認為,誕生于中國宋代的文學家蘇軾,如今是西方漢學家們探討最多的中國重要人物之一,他留下的文化遺產已成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。
文豪,首先在于蘇東坡的廣博。詩詞文書畫,蘇東坡無所不能,以詞論,他與辛棄疾并稱“蘇辛”,以文論,他與歐陽修并稱“蘇歐”,以書法而論,他與黃庭堅并稱“蘇黃”。
蘇東坡仁慈慷慨,光明磊落,浪漫開明,單純真摯,快樂歡愉,無憂無懼。他去世后大約一百年間,無數的文人為他立傳,只有自由馳騁、無拘無束的靈魂才能夠享受到他那份純真。
如果說有宋一朝是中國文明的一座高峰,那么毫無疑問,蘇東坡是中國文明高峰中的高峰。
1061年,24歲的蘇東坡被任命為大理評事,簽書鳳翔府判官。他寫出了《和子由澠池懷舊》:
人生到處知何似,應似飛鴻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,鴻飛那復計東西。老僧已死成新塔,壞壁無由見舊題。往日崎嶇還記否,路長人困蹇驢嘶。
文豪,其次在于蘇東坡的文風。他具有非凡的天分,敢于破除一切語言和體制的障礙,這種勇往無前的精神,又體現為其詩詞文的豪放。
關于蘇詞的總體風格,在蘇軾生前,論說甚多,見仁見智,有“清麗舒徐”(張炎《詞源·雜論》)、“韶秀”(周濟《介存齋論詞雜著》)、“清雄”(王鵬運《半塘遺稿》)等多種說法。
紹興辛未(1151),也就是蘇軾辭世后的半個世紀左右,“豪放”一詞始流行。最有影響的當屬豪放說,始見于曾慥跋《東坡詞拾遺》:“豪放風流,不可及也。”
明代張綖在《詩余圖譜》中堅定地論述:“蘇子瞻之作,多是豪放。”清代郭麐有言:“(詞)至東坡,以橫絕一世之才,凌厲一代之氣,間作倚聲,意若不屑,雄詞高唱,別為一宗。”(《靈芬館詞話》卷一)蔣兆蘭也說:“自東坡以浩瀚之氣引之,遂開豪放一派。”(《詞說》)
蘇詞之豪放精神首先體現在追求一種奔放不羈、縱情放筆、適性作詞的創作境界,恰如他在《晁錯論》所述:“古之成大事者,不惟有超世之才,亦須有堅忍不拔之志。”
在詞的創作中,蘇軾一任性情,或者說“氣”的抒發,因此其詞體現出的風格形式難免與傳統觀念——詩莊詞媚——相左。蘇詞的豪放并不在于其內容有多少豪壯的成分,而在于它能超越固有觀念,從而直抒胸臆,自訴懷抱,能“新天下耳目”(王灼《碧雞漫志》卷二)。
明月幾時有,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,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風歸去,又恐瓊樓玉宇,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間。轉朱閣,低綺戶,照無眠。不應有恨,何事長向別時圓?人有悲歡離合,月有陰晴圓缺,此事古難全。但愿人長久,千里共嬋娟。——蘇軾《水調歌頭》
莫聽穿林打葉聲,何妨吟嘯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輕勝馬,誰怕?一蓑煙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風吹酒醒,微冷,山頭斜照卻相迎。回首向來蕭瑟處,歸去,也無風雨也無晴。——蘇軾《定風波》
蘇詞豪放精神的另一個方面是吐納百川、沖決一切、淋漓直瀉的氣勢。這一點,陸游在《御選歷代詩余》的注解最為形象:“試取東坡諸樂府歌之,曲終,覺天風海雨逼人。”

蘇詞的豪放精神不同于后來的某些豪放派詞人,像陳亮、劉過等人,他們作品中的豪放氣息過于粗豪淺易,且缺乏內斂少余韻,而我們讀蘇詞除感受到“天風海雨”般氣勢外,還能深刻地體會到蘇軾至真至濃、至深至廣的人情味道,或曰“情味”——蘇詞的豪放精神如果沒有這種情味,那其藝術感染效果必然大打折扣。
他寫給妻子的詞《江城子》:“十年生死兩茫茫,不思量,自難忘。千里孤墳,無處話凄涼。縱使相逢應不識,塵滿面,鬢如霜。”一片深情繾綣。
他寫送別詞《臨江仙·送錢穆父》。這首詞是在宋哲宗元祐六年(1091)春,蘇軾知杭州(今屬浙江)時,為送別自越州(今浙江紹興北)徙知瀛洲(治今河北河間)途經杭州的老友錢勰(錢穆父)而作。當時蘇軾也將要離開杭州。
一別都門三改火,天涯踏盡紅塵,依然一笑作春溫。無波真古井,有節是秋筠。惆悵孤帆連夜發,送行淡月微云,樽前不用翠眉顰。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
這首詞一改以往送別詩詞纏綿感傷、哀怨愁苦或慷慨悲涼的格調。蘇軾批評吳道子的畫說: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。”這首道別詞里,蘇東坡宛如立在紙面之上,議論風生,直抒性情,寫得既有情韻,又富理趣。這種曠達灑脫的個性風貌,恰恰是蘇東坡的豪放之處。
蘇軾之情又是一種超越平常人的天才之情、曠達之情、豪放之情、因此在表達這種高情時,蘇軾作詞便如李白作詩,天才橫放,縱筆揮灑,自然流露而又無具體規范可循。這樣一來,東坡詞就成為抒發其人生豪情的“陶寫之具”,我自為之,橫放杰出,“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”(《苕溪漁隱叢話后集》卷33引晁補之語)。
蘇詞的豪放,可謂從心所欲不逾矩,在藝術規律的容許之下,讓創造力充分自由地活動,既如行云流水般自在活潑,同時又很嚴謹地“行于所當行,止于所不可不止”。錢鍾書說,李白之后,古代大約沒有人趕得上蘇軾這種“豪放”。
蘇東坡曾經用四個字來概括自己,或者說要求自己:“生、死、窮、達,不易其操。”今天,我們敬慕他的豪放,首先要理解他的豪放。這種豪放,不是一種完全無底線的無拘無束,而是一種有操守、有堅持、有定力、能力、魄力的放達。
二、博喻
蘇子詩詞的一大特色,莫過于比喻的豐富、新鮮和貼切:用一連串五花八門的形象來表達一件事物的一個方面或一種狀態。汪師韓《蘇詩選評箋釋》:“用譬喻入文,是軾所長。”
《百步洪》就是公認的反映他這一特色的杰作:
長洪斗落生跳波,輕舟南下如投梭。水師絕叫鳧雁起,亂石一線爭磋磨。有如兔走鷹隼落,駿馬下注千丈坡。斷弦離柱箭脫手,飛電過隙珠翻荷。四山眩轉風掠耳,但見流沫生千渦。險中得樂雖一快,何異水伯夸秋河。我生乘化日夜逝,坐覺一念逾新羅。紛紛爭奪醉夢里,豈信荊棘埋銅駝。覺來俯仰失千劫,回視此水殊委蛇。君看岸邊蒼
- 下一篇: 漢繡?唐繡?關于各朝繡花特點你知道多少?
- 上一篇: 這下誤會大了,這些千古名句原來是這個意思!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