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:恒星晝霣夜不見,江南釋教都總統楊璉真迦在宰相桑哥支持下,陸秀夫、張世杰擁宋端宗趙昰流亡海上。
冬青樹,山南陲,九日靈禽居上枝。知君種年星在尾,根到九泉雜龍髓。恒星晝霣夜不見,七度山南與鬼戰。愿君此心無所移,此樹終有開花時。山南金粟見離離,白衣人拜樹下起,靈禽啄粟枝上飛。
——謝翱《冬青樹引別王潛》
至元十五年,江南釋教都總統楊璉真迦在宰相桑哥支持下,開掘南宋六陵。
這一年,文天祥被俘,元軍平定東川。陸秀夫、張世杰擁宋端宗趙昰流亡海上,四月,年僅九歲的趙昰因驚病交加而死。陸、張復立趙昺為帝,此時距離崖山之戰,還有一年。
只要南宋未亡,在元軍鐵騎下哀號的中原百姓,就還有一線希望。
但在元廷眼中,宋朝已經是過去時了。
楊璉真迦身為僧侶,卻“怙恩橫肆,窮驕極淫”,幾個前朝皇帝的陵墓在他眼中不算什么。他命人大肆發掘諸陵,將陪葬品掠奪一空,又將宋理宗的顱骨制成飲器,其余帝王的尸骨,都散落在草莽之中。
自然沒人敢阻止他們。元廷已實際控制了中國大部分領土,幾場屠城下來,敢于反抗的人們也沒了聲音。在楊璉真迦眼里,這些文弱的江南人和草原上馴服的牛羊沒什么區別。
但是在發陵當晚,一個計謀已在平民與書生的附耳低語中成型。
當地的年輕人們趁著夜色,拿著注有各帝年號的木匣,潛入陵園,分別收集各帝的遺骨,再在天色未明時離開。這些從元朝僧侶的踐踏下搶救出來的遺骸,被偷偷掩埋在蘭亭山以南,上植冬青樹為記。
這個主意,是一個名叫謝翱的讀書人出的。
吹老單于月一痕,江南知是幾黃昏。
水仙冷落瓊花死,祇有南枝尚返魂。
——謝翱《梅花二首》其二
南宋朝廷并沒給過謝翱什么好處。他出身儒學世家,少有才名,十七歲赴臨安應進士試,不幸落榜——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他是幸運的,落榜讓他不用像很多文人一樣,把自己的名節終身和宋朝綁定。
中國古代文人的操守和女子的貞節,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處。入仕類似于出閣,前朝遺民就像守節的寡婦,而亡國后在新朝做官的文人就好比夫死再嫁的女子,在封建道德的視角下總是被人看低一眼。
謝翱在進士試中落榜,這讓他不必“失身”于一個即將滅亡的王朝。大廈將傾時不會有人指望他力挽狂瀾,無力回天后也不會有人要求他以死殉國。新朝建立后,統治者不會為了收攬人心逼他出仕,而如果他愿意出仕,身上也不會帶著背叛者的污點。他不必像文天祥和陸秀夫,把自己牢牢鎖死在一艘即將傾覆的大船上。他的人生還有無數可能,他還可以選擇自己的未來。
德佑二年正月,元兵攻陷臨安。文天祥傳檄各州郡舉兵勤王,聽到消息,二十七歲的謝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自己的未來。
他變賣家產,招募鄉兵,帶著這支小小的隊伍從家鄉出發,到南劍州投奔文天祥,被任命為諮議參軍。次年,元兵由浙入閩,謝翱跟隨文天祥轉戰兩廣、江西,最終不敵元軍,文天祥為保存抗元力量,令謝翱離軍歸鄉。
在文天祥身邊的幾年,是謝翱僅有的能為宋朝做點事的日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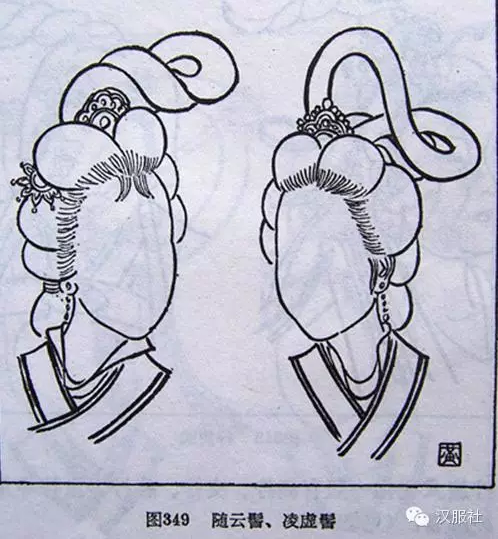
他有才華,有抱負,如果早出生幾百年,也許他能成為宋仁宗朝中諸多名臣中的一員;即使再晚些,也可以在南渡之后給驚魂未定的南宋王朝盡些力量,和李綱、趙鼎他們同處朝列,也不枉生為宋人。
但他生在這風雨飄搖的宋末,一切努力都沒有回報,一切希望都沒有結果,他能做的只是在聽到文天祥的死訊后大哭一場。
殘年哭知己,白日下荒臺。
淚落吳江水,隨潮到海回。
故衣猶染碧,后土不憐才。
未老山中客,惟應賦八哀。
——謝翱《西臺哭所思》
文天祥的死足以摧毀他最后的希望。宋朝不會再回來了,只能成為一個歷史名詞,和他曾在古書里看到的諸多朝代一樣,靜靜地躺在褪色的墨跡間。作為它的子民,他的一切愛恨都將失去價值,化為青史上幾行輕描淡寫的敘述。
但他仍然堅持了下去,就像冒著生命危險偷偷掩埋南宋諸帝的遺骨一樣。堅持本身就是意義。
宋亡后,謝翱隱居浙江,常獨自行游于浙水之東,見到與文天祥離別時相似的景物,便徘徊顧盼,失聲慟哭。他與志同道合的南宋遺民方鳳、吳思齊、鄧牧交游,成立“月泉吟社”“汐社”,把亡國之痛傾入詩文之中。在宋末遺民詩人中,他的成就最高,明代楊慎譽之為“宋末詩人之冠”。
閑庭生柏影,荇藻交行路。
忽忽如有人,起視不見處。
牽牛秋正中,海白夜疑曙。
野風吹空巢,波濤在孤樹。
——謝翱《效孟郊體》
元貞元年,謝翱病逝于桐廬,年四十七。
他的一生,都奉獻給了一個無法挽救的王朝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