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:吉服是明代形成的一個(gè)新的服飾分類,由傳統(tǒng)的“吉服”概念分化而來,指用于時(shí)令節(jié)日、婚禮、壽誕、筵宴等各種吉慶場合的服裝。到清代正式成為冠服制度中的一個(gè)專門分類。
吉服是明代形成的一個(gè)新的服飾分類,由傳統(tǒng)的“吉服”概念分化而來,指用于時(shí)令節(jié)日、婚禮、壽誕、筵宴等各種吉慶場合的服裝。到清代正式成為冠服制度中的一個(gè)專門分類。
傳統(tǒng)“吉服”指的是用于吉禮(重大祭祀等)的祭服,如冕服一類。隨著時(shí)代發(fā)展、節(jié)日與慶祝活動(dòng)的增多,就需要一套專門的“吉慶之服”來應(yīng)對(duì)各種喜慶的場合,因此明代就把用于嘉禮和各類吉慶場合的、比日常便服更為正式的服裝統(tǒng)稱為“吉服”。明代吉服盡管不見于制度,但在各類典章政書、文學(xué)作品中屢屢出現(xiàn),如《大明會(huì)典》記載:“圣節(jié)前三日、后三日,俱吉服。”《萬歷野獲編》卷五:“錦衣官侍朝,俱烏帽、吉服。”《金瓶梅》第三十九回描寫:“西門慶從新?lián)Q了大紅五彩獅補(bǔ)吉服,腰系蒙金犀角帶。”《醒世姻緣傳》第四十四回:“到了吉時(shí),請(qǐng)素姐出去,穿著大紅裝花吉服、官綠裝花繡裙、環(huán)佩七事,恍如仙女臨凡。”
明代的吉服并非單一的標(biāo)準(zhǔn)款式,其式樣與常服、便服相同,如圓領(lǐng)、直身、曳撒、貼里、道袍、 等,顏色多用大紅等喜慶色彩,如官員就是以大紅圓領(lǐng)作為吉服。吉服的紋飾通常比常服、便服更為華麗精美,大多使用應(yīng)景題材或帶有吉祥寓意的圖案、文字。
萬歷時(shí)期,南京御史孟一脈在給明神宗的上疏中說:“遇圣節(jié)則有壽服,元宵則有燈服,端陽則有五毒吉服,年例則有歲進(jìn)龍服。”壽服為帝后壽誕日所穿,多飾有“萬壽”等與祝壽有關(guān)的紋樣;燈服為元宵節(jié)所穿,使用燈籠紋樣;五毒吉服為端陽節(jié)所穿,飾有“五毒”紋樣;龍服即飾有龍紋的各式龍袍。這里提到的服飾都是比較典型的節(jié)日吉服,使用的圖案內(nèi)容均與穿著的時(shí)間、場合相對(duì)應(yīng)。
劉若愚在《酌中志》中詳細(xì)記錄了每個(gè)季節(jié)應(yīng)更換的衣服材質(zhì)以及不同月份的時(shí)令節(jié)日所使用的應(yīng)節(jié)圖案。如從年前臘月二十四祭灶之后,宮眷和內(nèi)臣便穿葫蘆景補(bǔ)子及蟒衣。三月初四日,宮眷和內(nèi)臣換穿羅衣。四月初四日,宮眷內(nèi)臣換穿紗衣。五月,初一日起到十三日,宮眷內(nèi)臣穿五毒艾虎補(bǔ)子、蟒衣。七月初七日,七夕節(jié),宮眷穿鵲橋補(bǔ)子。八月,宮中賞秋海棠、玉簪花。定陵出土有玉兔紋的補(bǔ)子,應(yīng)該是用于中秋。九月初四日,宮眷內(nèi)臣換穿羅衣,用重陽景菊花補(bǔ)子、蟒衣,同時(shí)抖曬皮衣,制衣御寒。十月初四日,宮眷內(nèi)臣換穿纻絲。十一月,賜百官戴暖耳。冬至節(jié),宮眷內(nèi)臣皆穿陽生補(bǔ)子、蟒衣。補(bǔ)子是貴族、官員們?cè)诔7ǔ3┑那靶亍⒑蟊郴騼杉缣幯b飾的圓形或方形的圖案,原本用來區(qū)別各自的身份、等級(jí),吉服的補(bǔ)子則可以使用應(yīng)景題材,不一定體現(xiàn)等級(jí)高低。
將現(xiàn)存的明代服飾、織繡實(shí)物與《酌中志》的描述對(duì)照,能更直觀地了解這些吉服紋樣的特征:
葫蘆景:從頭一年臘月二十四祭灶以后到新年都使用葫蘆景圖案,又稱大吉葫蘆,宮中使用的葫蘆景補(bǔ)子多和龍、蟒等裝飾在一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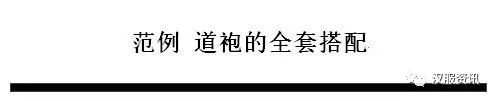
燈景:正月十五是元宵節(jié),又叫燈節(jié),這一天大家都要賞燈,因此衣服上也使用燈籠圖案,襯托出節(jié)日的喜慶氣氛。

五毒:五月初五是端陽節(jié),使用五毒(蝎子、蛇、壁虎、蜈蚣以及蟾蜍)的圖案,以提醒大家,進(jìn)入五月后毒物滋生,要早做預(yù)防。同時(shí)在圖案里加入了老虎、艾草的形象,象征“艾虎”,用來消滅五毒,因此帶有驅(qū)邪避害的寓意。

牛郎織女:七月初七是七夕節(jié),傳說在這一天牛郎、織女要在鵲橋相會(huì)。因?yàn)榕@伞⒖椗际翘焐系男撬蓿詧D案設(shè)計(jì)并沒有太多“浪漫”的地方,而是突出了他們“神”性的一面,造型穩(wěn)重而有氣勢(shì),非常符合宮廷的環(huán)境。

玉兔:八月十五是中秋節(jié),月圓之夜,圖案中往往有玉兔、滿月等。

菊花:九月初九為重陽節(jié),這一天宮中要登高、飲菊花酒。此時(shí)正逢秋季菊花開放,所以用菊花紋樣來體現(xiàn)節(jié)令特征。

陽生:冬至節(jié)是古代比較重要的節(jié)日,過了冬至,春天即將到來,陰氣逐漸下降,陽氣開始生發(fā)。在設(shè)計(jì)圖案時(shí)用口中吐出上升瑞氣的羊來表現(xiàn)“陽、生”的諧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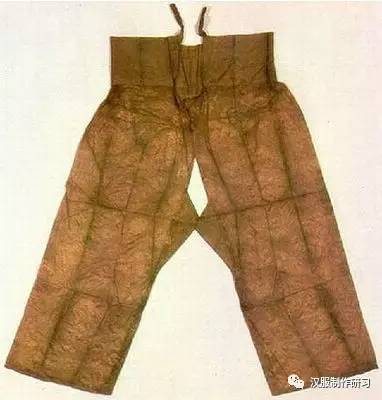
冬季還使用綿羊太子圖案。雜劇《鬧鐘馗》里描寫:“三陽真君領(lǐng)三個(gè)綿羊太子。”《酌中志》也提到宮中在冬至節(jié)時(shí)“室中多畫綿羊引子畫貼”。三個(gè)綿羊太子諧音“三陽開泰”,也有一個(gè)綿羊太子引領(lǐng)一群小羊的,稱為“綿羊引子”。如明代繪畫中,綿羊太子頭戴狐帽(韃帽)、身穿有毛皮出鋒的罩甲和織金通袖袍,是冬季戎裝打扮,肩頭扛著梅枝,上掛鳥籠,籠內(nèi)為喜鵲,寓意“喜上眉梢”,身騎大羊,周圍簇?fù)碇蝗盒⊙颍笳髯铀梅笔ⅲc“百子圖”寓意相同(定陵出土有孝靖皇后的“百子衣”)。

自古人們便追求健康長壽,因此與祝壽有關(guān)的紋飾相當(dāng)常見。帝后們的萬壽節(jié)、千秋節(jié)較之常人更為隆重,留下了很多用于壽誕的吉服實(shí)物。慶壽題材一般使用靈芝、仙鶴、壽桃等,組成“靈仙祝壽”等帶有吉祥寓意的圖案。或者大量裝飾“壽”、“萬壽”等文字,將壽誕日的美好愿望更為直白的表達(dá)出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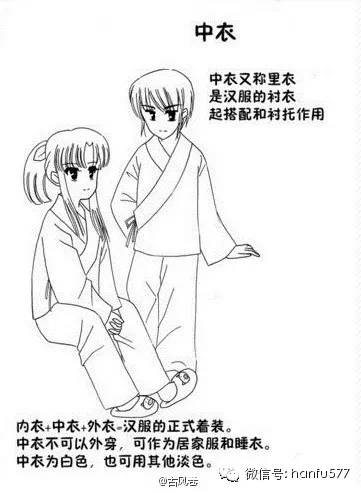

明代吉服紋樣的設(shè)計(jì)巧妙之處還在于能夠以組合的方式,將不同題材融合成一個(gè)更具“個(gè)性化”的喜慶圖案。如選擇與壽誕日期比較接近的時(shí)令節(jié)日,將應(yīng)節(jié)圖案與慶壽圖案組合起來,給人以“喜上加喜”、“雙喜臨門”的感覺,讓節(jié)日里的歡樂氣氛更加濃厚。比較典型的是明神宗的生日紋樣。神宗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(公元1563年9月4日),恰好在中秋之后,于是宮中就將用于皇帝萬壽圣節(jié)的“壽”紋和用于中秋節(jié)的“玉兔”放到了一起,定陵出土的明神宗帝后服飾中就有很多造型可愛的玉兔形象。

由于吉服以突出視覺效果為主,又符合大家崇尚喜慶、吉利的心理,所以在紋樣使用時(shí),允許一定程度上突破等級(jí)約束,朝廷并不作過多干預(yù),所以明代出現(xiàn)的服飾僭越現(xiàn)象往往在吉服上最為突出,如士庶女子穿戴鳳冠蟒袍、官員吉服出現(xiàn)五爪蟒龍等等。《舊京遺事》記載:
“或有吉慶之會(huì),婦人乘坐大轎,穿服大紅蟒衣,意氣奢溢,但單身無婢從,卜其為市傭賤品。上無尊卑等級(jí)之差,下有耗財(cái)費(fèi)力之損,富給不可得也。都中婦人尚袨服之飾,如元旦、端午,各有紗、纻新衣,以夸其令節(jié)。麗者如繡文然,不為經(jīng)歲之計(jì),羅裙繡帶,任其碧草、朱藤,狼藉而已。每遇元夕之日、中秋之辰,男女各抱其綺衣,質(zhì)之子錢之室,例歲滿沒其衣,則明年之元旦端午,又服新也。”
這里就說到這些僭越等級(jí)、極其奢華的衣服,大多用在吉慶之會(huì)和時(shí)令節(jié)日里,而且特別講究是新衣,在節(jié)日穿過后,就拿到典衣鋪當(dāng)了,不去取贖,拿這些錢去置辦下一年過節(jié)的新衣。盡管這里沒有特別提到“吉服”一詞,但從中可以看出具有專門功能的吉服,是基于生活的需要、人們的消費(fèi)觀念及當(dāng)時(shí)的物質(zhì)條件而產(chǎn)生的,與日常生活所穿便服有很大區(qū)別。
吉服的典型裝飾有兩種,一種是明代最常見的云肩、通袖襕、膝襕紋樣。衣身在前胸、后背、兩肩處裝飾有柿蒂形的“云肩”,從左右肩部至袖端裝飾有“通袖襕”,前后襟下擺裝飾有“膝襕”,故也將這類吉服稱為通袖袍或膝襕袍。其紋飾多較尊貴,如飾以蟒、斗牛、飛魚、麒麟、鳳、翟、仙鶴等祥禽瑞獸圖案。

另一種裝飾是對(duì)后世影響較大的八團(tuán)紋樣,即在前身與后身各裝飾三個(gè)團(tuán)紋,呈“品”字形分布,在兩袖(上臂處)各裝飾一個(gè)團(tuán)紋。以八團(tuán)紋樣為基礎(chǔ),可以發(fā)展出十團(tuán)、十二團(tuán)等多團(tuán)紋樣。到清代,八團(tuán)就成為吉服的基本紋樣了,一直延續(xù)到民國時(shí)期。此外,戲曲中的“蟒”仍保持這種紋飾特征。


吉服紋樣到近代也發(fā)生了很多變化,根據(jù)各自審美與需要,紋飾可繁可簡,但不論如何變化,吉服所具有的正式、喜慶等特征都十分明顯。在現(xiàn)代社會(huì)中,人們也有應(yīng)對(duì)各種社交場合或儀式的服裝,像結(jié)婚時(shí)穿的西式婚紗、禮服,或傳統(tǒng)式樣的鳳冠霞帔、長衫,以及前幾年比較流行的、在春節(jié)等節(jié)日穿的改良“唐裝”等等,都可算作“吉服”的概念,這也反映出今人仍有對(duì)吉服的實(shí)用需求。隨著能體現(xiàn)民族文化的服飾不斷受到國人的關(guān)注,傳統(tǒng)服飾中的圖案運(yùn)用、著裝理念也可以給今人的設(shè)計(jì)帶來一些啟發(fā)。
- 下一篇: 唐朝服飾的常見紋樣
- 上一篇: 中華古代帶制簡述(上)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