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:久困科場的袁中道參加了在京的會試,但念老父及兩兄皆不及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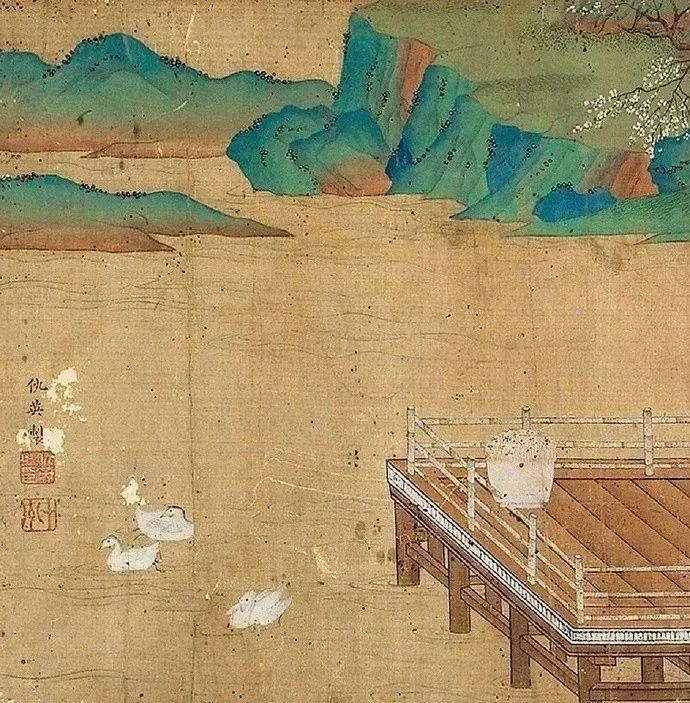
萬歷四十四年,久困科場的袁中道參加了在京的會試,放榜之日,終于“得中試捷音”。
此時他四十七歲,回首往事,十六歲考中秀才可謂少年得志,然而三十年間六次鄉試、四次會試,昔日奮跡云霄的志向日漸消磨。行將半百,功名珊珊遲來,怎不由他心生感慨:
予奔波場屋多年,今歲不堪其苦,至是始脫經生之債,亦甚快。但念老父及兩兄皆不及見,不覺為之淚下。——袁中道《游居杮錄》
四年前,老父去世;七年前二兄宏道去世;十六年前長兄宗道去世。無怪乎中道“淚下”,公安三袁,同樣文章聲聞海內,然而相對于兩位兄長科場之路的順遂,他的進士及第實在等得太久。
壹
隆慶四年,家住湖北公安之長安里的秀才袁士瑜,又得一子。長子宗道十一歲,次子宏道三歲,而今新生之子取名中道。
袁士瑜歡喜非常,但更令他歡喜的是他很快發現三個孩子都有項橐之才。
宗道十歲即能賦詩,宏道四歲已能屬對,中道十一歲作《黃山》《雪》二賦,下筆凡五千言。公安三袁之名,漸播漸遠。
萬歷二十一年,兄弟三人赴麻城一同拜訪了鼎鼎大名的李贄。李贄評說他們:“伯也穩實,仲也英特,皆天下名士也”。
三人中又以中道少年英氣,極得父兄厚愛,宗道在《答梅開府先生》書中說:“三弟,愚兄弟中白眉也,阿兄頗心遜而私賞之”。
中道率性灑脫,但陡遇挫折也難免郁悶寡歡。六年前長兄宗道會試第一,選庶吉士,授翰林院編修,前一年二兄宏道進士及第,中道卻已鄉試兩次落榜。苦悶無由排遣,中道有了人生中第一次吳越之游。
在拜訪李贄后,中道和好友丘長孺買舟東下,人生中快意瀟灑的自我放逐開始了。
貳
袁宏道在《龔惟長先生》書中說:
“目極世間之色,耳極世間之聲,身極世間之鮮,口極世間之譚,一快活也。”
這種極世間聲色的生活觀,中道深得旨趣。如果說第一次吳越之游,中道意在一抒胸中抑郁之氣,那么第三、第四次鄉試落第后的中道的兩次吳越之游,顯然是頹然其中了,尋名山,訪勝友,左美酒右佳人,笙歌宴飲、詩酒茗談中,樂而忘返。妙筆依舊生花,而自作曠達的悲涼意味亦顯現無遺。
春光秋月盡可度,最是宅邊桃葉渡。夜飲朝歌劇可憐,繁華極是傷心處。領略東風快放顛,任罵輕薄惡少年。閑來乞食歌妓院,竿木隨身掛水田。沉湎放肆絕可笑,鄉里小兒皆相誚。君不見擘天金鳷啖老龍,榆枋小鳥難同調。——袁中道《放歌贈人》
客游之中如此,居家之日亦時時買醉。宗道在《致三弟》書中說:
“邑中人云:弟日來常攜酒人數十輩,大醉江上,所到市肆鼎沸。以弟之才,久不得意,其磊塊不平之氣固宜有此。然吾弟終必達,尚當靜養以待時,不可便謂一發不中遂息機也。”
以酒解憂、好游成癖、流連歡場,以消胸中壘塊不平之氣,既是科場失意使然,亦因于性情,更源于晚明士風熏染。
明代苛政積弊之多,為歷代所不及。萬歷朝權利集團的傾軋、吏治的腐敗,使得國運日下。理學對思想的束縛,促使了心學在下層的盛行。李贄的肯定人欲、鼓出自由、追求真實自我的思想直接影響了三袁。
袁中道正是在這種環境下任情恣性,閑拋閑擲著自己的才情與光陰。
叁
萬歷二十八年,袁中道應順天府鄉試再次落第,十一月二十六日得京中宗道訃音,長兄規戒之言猶在耳際,卻是人天永隔,中道撫膺大叫,悲慟不已。臘月初赴京料理喪事,次年四月扶柩水路回公安,備極艱辛。對兄長,中道是深情的,以致多年后見到宗道遺詩,猶淚如雨下。
和中道同時扶柩歸來的還有任職禮部乞假回公安的宏道。較之宗道,中道和宏道的性情才識更為接近,他們除了是兄弟更是同學、知己,也是詩文創作上的盟友。

對李夢陽、李攀龍“前后七子”的復古模擬主張,三袁提倡詩文創作須“從自己胸臆流出”,寫“本色獨造語”,所謂“獨抒性靈,不拘格套”。三人的詩文,宗道開風氣之先,領袖無疑是宏道,中道則推波助瀾。
大運無終盡,細柳不常灼。金樽盛美酒,郁郁胡不樂。以手摸頭顱,隆隆一具骨。暫時屬我身,誰知非我物。轉盼忽如電,微軀戢一木。烏鴉鳴其上,青蛙叫其足。白蟻如白粲,行行相蝕駁。——袁中道《 詠懷四首 其五》
宏道在《敘小修詩》中論中道詩說:
“……非從自己胸臆流出,不肯下筆。有時情與境會,頃刻千言, 如水東注,令人奪魄。其間有佳處,亦有疵處。佳處自不必言,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……”
宏道居家期間,和中道或宴客或出游,二人觴詠詩文、切磋學問,兄弟怡怡,這是他們人生中難得的時光。
萬歷三十一年中道鄉試中舉,但喜悅停留時間并不長,緊接著是兩次會試落第。落第后,中道又向往起散心抒懷、滌浣俗腸的遠游生活,在宏道返京任職后的萬歷三十七年,中道再次東游吳越。
肆
這一次吳越之游經漢陽、過金陵、走鎮江、抵揚州,一路之上,袁中道探古尋幽、問學會友,所過之處,援筆為記。
同我真往游棲霞山。山去燕子磯三十里,途中黛色層疊,包絡田疇,因憶靖節“平疇交遠風,良苗亦懷新”之句。至山,寓老宿蒼麓禪室。樓后開窗,見巉巖有落勢,亦一佳處。躡徑過石梁,尋中峰澗道,石皆為中貴所鑿,如蜂房,令人欲嘔,遍尋山中佳石皆損。至乳泉,啜一盞而行。下至千佛巖,巖亦架以閣,重墻圍繞,舊時佳本皆伐去。品外泉溷濁,不復上沸。路如永巷,令人一步一恨。過方丈,由小門入大殿禮佛。樹色皆為重墻所隔,時日如炙,急往覓天開巖,息于珠泉。過般若臺,坐叢桂下,行亂石澗邊,石多太湖者。喬松夾路,遠望巖壑,了不可測,甚有幽意。抵巖,巖石巉巉,數月前忽中裂一片塞路。巖下為好事者刻禹碑,作一石墻置之,大損石趣。歸,納涼于白蓮池上。時白蓮盛開,香風滿一山。 ——袁中道 《游居杮錄》
游山玩水固然逍遙,求取功名依然繼續。為萬歷三十八年的春試,中道由揚州北上赴試。時乖運蹇,中道又一次落榜,宏道陪中道一同南歸公安。

七夕后,中道欲籌劃遠游時,宏道偶發火病。中秋后,宏道火病漸加,中道始惶惶不安,朝夕省視,臥不交睫。九月初六日,宏道一睡不醒,闔然而逝,中道痛不欲生。
痛哉痛哉!一朝遂失仁兄,天崩地裂,以同死為樂,不愿在人世也。予亦自絕于地,久之始蘇,強起料理棺木。——袁中道《游居杮錄》
此后數年,中道都無法走出兄亡的悲痛,喪葬事宜亦數年奔波。復觀海內知交,也半已零落,不幸接連發生,萬歷四十年春,老父袁士瑜也去世了。
閉門清坐,微月蒙蒙。坐紫荊花下,內悲父兄,外悼友朋,因病戒酒,寂寂無一人往來可以倡和者,不知余生何以度日。——袁中道《游居杮錄》
父兄長逝,自己多病之身,一事無成,料理家事亦只能坐看田產散盡,悲痛悔恨,又于事何補?
伍
為父守孝三年后,萬歷四十四年,中道終于進士及第。正如中道自己所說,及第只是一了經生之債。

自萬歷四十六年起,在連任徽州府教授、南京禮部主事、南京禮部郎中幾個虛職后,袁中道以疾辭官。天啟六年,五十七歲的袁中道病逝于南京。
中道才高情深、也率性任真;他有關心民謨的理想,也渴望俗世的富貴;蹉跎場屋,抑郁愁牢,耽于酒色,以至多病,極戀繁華,又心中向道。今人季維齋說“以清苦粹然之趣盱衡之,小修不免為俗子。實則以大道觀之,小修確為俗子也。”
生逢江河日下的大明王朝,沒有顯貴的功名、沒有拏云的事業,但作為公安派重鎮,俗子袁中道留下的是他不羈的生平和不朽的詩文。
END
作者丨方名
編輯 | 詹茜卉校對 | 古月排版 | 李媛
- 下一篇: 加盟漢服店多少錢?
- 上一篇: 這七個中國男人,活成了頂級傳說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