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:漢武帝時代最突出的特點是人才輩出,他們出身底層, 極具冒險意識、進取精神,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衛青、霍去病。

漢武帝時代最突出的特點是人才輩出,他們出身底層, 極具冒險意識、進取精神,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衛青、霍去病。這些平民精英建功立業,迅速崛起,“蓋世必有非常之人,然后有非常之事;有非常之事,然后有非常之功。”這是一個由眾多“非常之人”建立“非常之功”的時代。
1、小人物的崛起
衛青、霍去病出身低賤,具有極強的冒險、進取精神,全憑個人能力與軍功不斷獲得封賞,越級提拔,直至位極人臣,他們二人是這些“小人物”的最杰出代表。“小人物”沒有家世背景,只能憑借個人能力與功勞獲得升遷,因此積極進取,勇于開拓,極富創造力,這些正好符合漢武帝改弦更張、創立不世之功的要求。
漢武帝的“內朝智囊團”就是由他提拔的平民精英組成的,他們足智多謀,當以丞相為首的外朝提出某項決策方案,漢武帝就讓內朝扮演“反對黨”的角色詰難辯論, 這些人中包括了莊助、朱買臣、主父偃、吾丘壽王等。
朱買臣與莊助都是會稽郡吳縣(今江蘇省蘇州市)人, 雖然家中貧窮,但愛好讀書,不治產業,以砍柴為生,常常一邊擔著柴薪走路,一邊讀書朗誦。他的妻子跟在他身后,好幾次阻止他,但朱買臣越來越大聲,妻子覺得羞恥, 要求離婚。朱買臣笑著說“我50歲時就要富貴,如今已經40 歲多了。你受苦太久,等待我富貴了會報答你。”妻子憤怒地回答道“像你這種人,只會在溝渠中餓死,哪里能富貴!”朱買臣眼看無法挽留妻子,就答應了離婚。過了幾年,朱買臣去長安詣闕上書,但很久得不到答復,連飯都沒有吃,幸虧同鄉莊助引薦,得以見到漢武帝,為他解說《春秋》和《楚辭》,深受漢武帝賞識,拜為中大夫,并成為內朝侍中。前妻自殺后,朱買臣還給了她丈夫安葬的費用。他又召見了所有當年給他飯吃、有恩于他的故人,一一報答。

漢朝選拔人才,一開始是任用開國功臣集團,即司馬遷所說的“自漢興至孝文二十余年,會天下初定,將相公卿皆軍吏”。漢景帝執政后期,開始任用漢文帝的舊臣、因平定七國之亂而封侯的新一代軍功貴族建陵侯衛綰為丞相,直至漢武帝繼位后才被罷免。漢朝開國后的80余年里,除一位外戚貴族外,擔任丞相的都是軍功貴族或其世襲侯爵的子孫,直至平民丞相公孫弘的出現。
公孫弘是一位儒生,大器晚成,早年在海邊放豬為生。建元元年(公元前140年),漢武帝剛剛即位,招納天下賢良、文學之士,年已花甲的公孫弘被招為博士,但后因出使匈奴不稱職被免。十年后的元光五年(公元前130年), 已是古稀之年仍舊“狀貌甚麗”的公孫弘被家鄉菑川國推舉,應征文學之士,因對策被漢武帝賞識,以第一名再次成為博士,后來被提拔為御史大夫,直至元朔五年(公元前124年),以高齡被任命為丞相,并被封為平津侯。

另一位深受漢武帝賞識的平民精英是主父偃,他是齊國臨菑人,屬于縱橫家學派。他生活一直不如意,窮困潦倒。元光元年(公元前134年),他到達長安,投在了衛青門下,仍然不得志,錢財早已用盡,但久居不去,因此其他門客都很討厭他。主父偃感到山窮水盡,便直接去宮門給漢武帝上書,不想早晨上書,當天傍晚時分就被漢武帝召見。主父偃最重要的建議是“推恩令”和主建議漢武帝不要放棄衛青收復的秦朝故土河南地,這些建議都被漢武帝采納。主父偃是個性乖戾張揚,過分恃才傲物,蔑視社會規則,又急功近利,急于建功立業,結果不久之后,便因為逼死了齊王,又向諸侯索取賄賂,而被擔心遭他陷害的趙王告發,以致最終被族誅。

這也許是平民精英難以避免的缺陷,他們在底層窮困太久,心理失衡,忌恨上層,一旦上位,出于補償心理, 得志便猖狂,個性張揚,不管不顧,沒有原則。一度被漢武帝器重的莊助、朱買臣、吾丘壽王最終都被誅殺,絕非偶然。
2、世家大族與平民精英的沖突
公孫弘常常與公卿大臣商量好了意見,但到了漢武帝面前,如果發現形勢不對,就會立即背棄與群臣的約定,順從漢武帝。但公孫弘并非一無是處,他曾竭力主張放棄經營西南夷,放棄設置朔方郡、滄海郡(治所在今朝鮮)而未果,于是勸漢武帝至少放棄西南夷、滄海郡而集中力量經營朔方郡。這是漢武帝從政期間做的一件節省民力的善事。漢武帝并不指望公孫弘這個丞相真的能做什么經天緯地的大事,真正的軍國大事實際全由他自己乾綱獨斷,公孫弘只是一個擺飾,丞相也只是備位而已。
漢武帝敬重的其實是汲黯這樣剛正不阿的人。汲黯的家族歷經了周、秦、漢三朝,創造了一個驚人的紀錄—“十世為公卿”。他為人傲慢,不講究禮數,會當場讓人下不了臺, 因此人緣不好,但他愛憎分明,直言敢諫;他信奉黃老學說,為官清靜無為,但注重民生,在太守任上,將東海郡治理得井井有條。一次河內郡(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縣)失火,燒毀了1000余戶人家,漢武帝派遣汲黯前去視察,他回來報告說“火災不足憂,但是現在河內一萬余家百姓被水旱災害波及,發生了父子相食的情況,我就見機行事,手持天子符節,將河內郡倉庫中的糧食發放給了災民。現在請陛下治我矯詔之罪。”
漢武帝認為汲黯做得正確,沒有治他的罪。漢朝法治嚴厲,矯詔是重罪,汲黯這樣做,是將百姓疾苦放在了個人生死之上,與那些以損害民眾利益來取悅上級的官員真是天差地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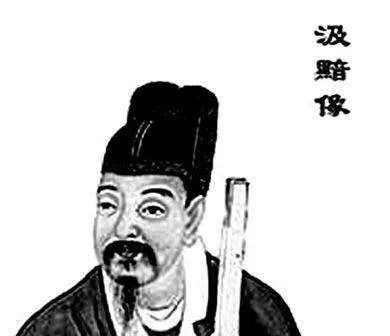
漢武帝殺伐決斷,視臣民性命如草芥,在他執政的54年里,除了汲黯,幾乎沒有其他人敢這樣頂撞他。他很了解汲黯的為人,一次他問莊助對汲黯的看法,莊助回答說“汲黯的行政能力一般,但卻非常有原則性,不為利益、威嚇所動,適合輔佐少年君主,維護社稷。”漢武帝點頭稱是“古有社稷之臣,至如黯,近之矣。”
為了征伐四夷,恢復秦朝版圖并開疆拓土,就必須要實行中央集權,以便能更有效地集中各種資源,漢武帝提拔、重用有一技之長的平民精英就是為此。

汲黯與公孫弘、張湯間的矛盾不僅是個人之間的矛盾, 也是世家貴族與平民精英之間的矛盾,是這一時代大背景的生動反映。在這一大轉型的時代,世家貴族開始沒落,平民精英快速崛起,兩者發生了激烈的矛盾,平民精英動搖了世家貴族對政治資源的壟斷,兩者間的矛盾是難以調和的。
如果將漢朝看成是一家公司,漢武帝就是一位絕對控股、握有最高權力的董事長兼CEO,他的管理風格是大膽進取,積極開拓市場,特別熱衷于兼并其他公司;他手下的大臣們就是各級的部門經理或業務員,漢武帝總是分派給他們極高的業務指標,完成了就重賞(封侯),失敗了輕則降級(除爵),重則開除(死罪)。由于賞罰極為分明,一些積極進取的底層職員常常能提出一項項極富創意、膽略但會遭到他們上級主管反對的項目計劃,這些計劃總是能得到董事長兼CEO的大力支持,而且總是能獲得成功。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,對于對手們來說,這種公司實在是太可怕了。

汲黯對漢武帝的評價“內多欲而外施仁義”可謂一針見血。人人都有欲望,馬斯洛理論將人的欲望需求按層次從低到高分成了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社交需求、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。漢武帝貴為天子,前四類的欲望需求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實現,他所追求的是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,即對內大一統、對外征服四夷、開疆拓土。因此強調清心寡欲的黃老學說不能滿足他的需要,雖然儒家學說強調大一統符合他的理想,但儒家同時強調“王道”,強調道德禮義的教化,需要施行仁政,君主更要以身作則,成圣成仁,這要求君主克制自己的欲望,不能好大喜功,顯然,儒家學說也不能完全滿足漢武帝的需要,他真正信奉的是“霸、王之道”。
西漢繼承了秦朝的嚴刑峻法,到了漢武帝時期,更是嚴厲打擊豪強、權貴,這不僅是為了抑制貧富分化,維護中央集權的權威和國家的統一,也是為了在官僚掌握大量資源的背景下有效抑制貪腐,雖然方法非常簡單粗暴,但在缺乏先進技術手段的前提下,卻行之有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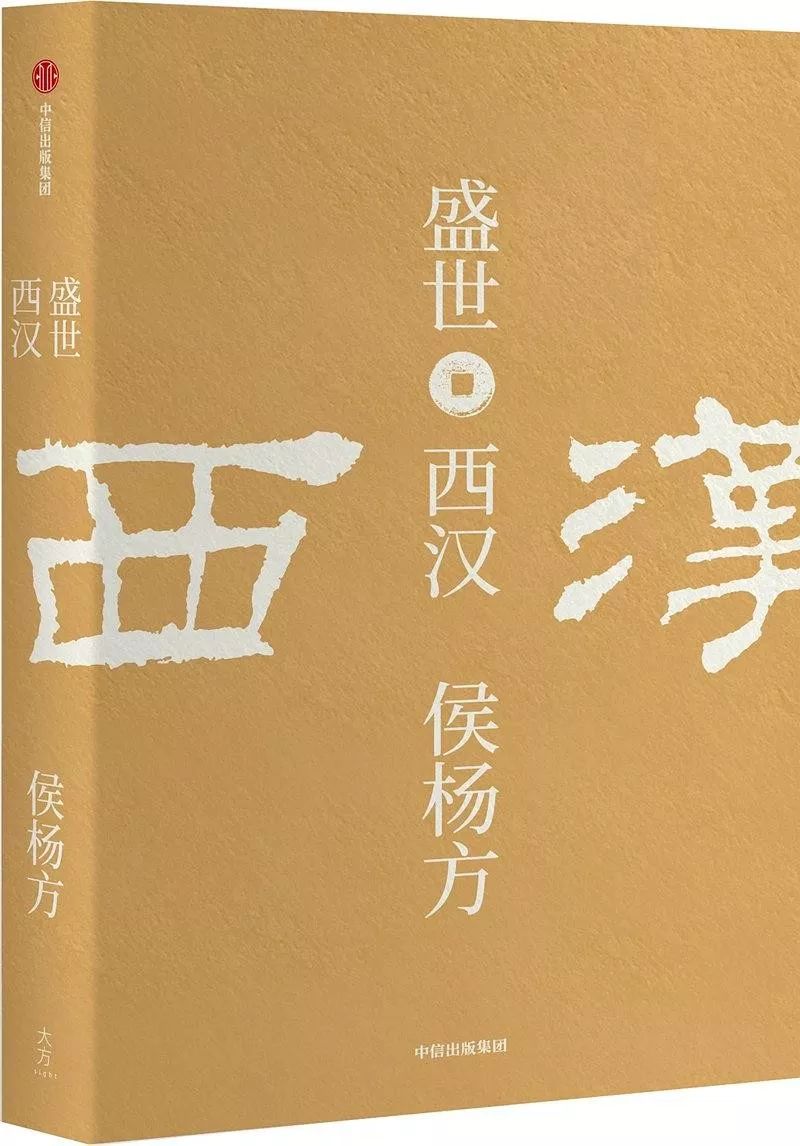
《盛世:西漢》
作者: 侯楊方
出版社: 中信出版集團2019-6
- 下一篇: 【知識分享】苦夏難熬,古人如何過夏天!
- 上一篇: 【人文歷史】這首中國最幽默的打油詩,專治無趣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