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:作為華夏第一批提倡要重視教育的民辦校長(zhǎng),孔子、墨子、莊子都收獲了很多求知欲強(qiáng)的弟子。
作為華夏第一批提倡要重視教育的民辦校長(zhǎng),孔子、墨子、莊子都收獲了很多求知欲強(qiáng)的弟子。
每年的開學(xué)第一課,諸子百家的先師們都循循善誘,請(qǐng)學(xué)生們?cè)谡n堂上一定要踴躍發(fā)言,遇到不懂的,不能憋在心里,要善于提問。特別還要加強(qiáng)獨(dú)立思考的能力,俗話說,“學(xué)而不思則罔,思而不學(xué)則殆”,要中和才行。
有了思考后,為免自己的思維太過天馬行空,跑偏了軌道,就要多和同學(xué)及老師交流,在交流中,多個(gè)獨(dú)立的靈魂在交匯,說不定能碰撞出新的高度。
學(xué)生們深以為然,于是,無論是儒家、墨家,還是道家,都涌現(xiàn)出來了一些極具獨(dú)立思考能力的學(xué)生,經(jīng)常能和老師產(chǎn)生充滿智慧的對(duì)話。
比如,儒門弟子子貢常向老師提問: 子貢曰:“貧而無諂,富而無驕,何如?”
子曰:“可也。未若貧而樂,富而好禮者也。”
子貢:貧窮卻不去做諂媚別人的事,富貴但從不以此驕傲,這樣的人怎么樣呢? 孔子:不錯(cuò),不過還不如貧窮內(nèi)心也快樂,有錢了也講禮守禮。
子貢問君子。
子曰:“先行其言而后從之。”
子貢問怎樣做一個(gè)君子,孔子說:“你想說的話,先腳踏實(shí)地做到了,再來宣布于眾,這樣的人就是君子。”
孔子總是能給學(xué)生醍醐灌頂式的指導(dǎo),但有時(shí)候,學(xué)生中也有不少思維角度刁鉆的人,總能給老師們醍醐一灌,淋了一身濕。
比如墨家的巫馬子和跌鼻。
墨家學(xué)生花式刁難
墨子的主要主張是兼愛非攻,和學(xué)生們講課,也是從這一母題無限延伸,說得多了,有個(gè)叫巫馬子的學(xué)生禁不住疑問:“你說兼愛天下,并沒有看到什么有利的,我不愛天下,也沒什么害的。兩者都沒效果,為什么你只認(rèn)為自己正確,而覺得我是錯(cuò)的呢?”
戰(zhàn)國(guó)時(shí)期的老師,都很善于舉例講故事,墨子回答說:“假如有個(gè)人在這里放火,一個(gè)人拿著水準(zhǔn)備去澆滅火苗,一個(gè)人舉了火把打算讓火燒得更旺,都還沒有做,只是準(zhǔn)備這樣做,這兩個(gè)人你更認(rèn)可哪個(gè)?”

巫馬子很實(shí)誠(chéng):“我覺得捧水的人行為是正確的,拿火的人是錯(cuò)的。”
墨子說:“對(duì)啊,我也認(rèn)為我兼愛天下是對(duì)的,而不是不愛天下。”
巫馬子說:“你說的兼愛,我還是覺得不對(duì)啊。人跟人的感情怎么可能完全無等差?比如我愛隔壁鄒人比愛偏遠(yuǎn)地區(qū)的越人多,愛魯人比愛鄒人多,愛我家鄉(xiāng)人比愛魯人多,愛我家人比愛我家鄉(xiāng)的人多,愛我爹媽比愛家里其他人多,愛我自己又比愛爹媽多一點(diǎn)……這都是從我個(gè)人立場(chǎng)自然有的想法。打我,我會(huì)痛,打別人,又不痛在我身上,我為啥要把別人家棺材搬到自己家里哭?替別人痛?所以,遇到緊急時(shí)刻,我只會(huì)殺別人保全自己,不會(huì)殺自己去利別人。”
其實(shí),巫馬子的話“愛有等差”是世界上最自然的感情,人的感情必定更關(guān)愛自己親近的人,可墨子也沒被問倒。
墨子:“你這個(gè)想法,你打算公諸于世,還是自己藏在心里想想?”
巫馬子:“我又沒說錯(cuò),我為啥要藏著掖著?”
墨子說:“嗯,那么問題來了,如果有一個(gè)人支持你的主張,那一個(gè)人就會(huì)在二選一的時(shí)候殺你而利自己,十個(gè)人推崇你的想法,那就有十個(gè)人會(huì)殺你利自己,天下人都喜歡你的主張,天下都來殺你……反過來,一個(gè)人不認(rèn)可你的主張,這一個(gè)人就要?dú)⒛悖驗(yàn)樗X得你散步的是不和諧的言論,有十個(gè)人不認(rèn)可,那十個(gè)人就要?dú)⒛悖煜氯?hellip;…總而言之,認(rèn)不認(rèn)可你主張的,都要?dú)⒛悖裁唇械湉目诔觯@就是啊。”

《墨子》沒記錄巫馬子后面怎么反駁,因?yàn)樗悄雍推渌T徒編輯的。但顯然,墨子的辯論存在巨大的漏洞,首先,巫馬子并不主張到處殺人,只是在我與別人之間必須二選一的時(shí)候,人必然是選擇自己優(yōu)先;其次,認(rèn)可巫馬子主張的,為什么就會(huì)殺巫馬子?二選一的情況不是隨時(shí)發(fā)生,即使人生有時(shí)會(huì)遇到,也并不是每個(gè)人都能和巫馬子處在“必須二選一”的情況;最后,不認(rèn)可巫馬子主張的,僅僅因?yàn)樗f出了自己內(nèi)心的真實(shí)想法就去殺他,他們得處于怎么樣的亂世啊。不喜歡和動(dòng)手殺人也沒有必然關(guān)系,這中間差了一個(gè)太平洋的距離。
除了巫馬子,墨子門下善于給老師提問的還有不少人,有一個(gè)叫跌鼻的也是其中翹楚。 有一次,墨子生病了,跌鼻很奇怪,因?yàn)槟油瞥绻砩瘢J(rèn)為鬼神對(duì)人間有監(jiān)視,他們賞善罰惡,對(duì)做壞事的人才進(jìn)行懲罰。于是跌鼻問:“先生說過,鬼神都是很明智的,能看見人間萬事萬物,也能給人間降災(zāi)降福,做好事的就會(huì)得到獎(jiǎng)賞,做壞事的就會(huì)得到懲罰。可先生你是圣人啊,為什么鬼神還讓你得病?是先生你說得不對(duì),還是鬼神并不那么明智,亦或是……”跌鼻沒好意思問出來的是:老師你不會(huì)瞞著我們做壞事了吧……
墨子沒好氣,自己生病了,弟子不關(guān)心病情,反而跑來諷刺,回答說:“我生病跟我主張的鬼神明智有啥關(guān)系?人生病的因素很多,鬼神只是監(jiān)視人間,進(jìn)行獎(jiǎng)罰的其中一個(gè),就像房間里有很多扇門,沒這扇門,還有很多種讓人生病的渠道呢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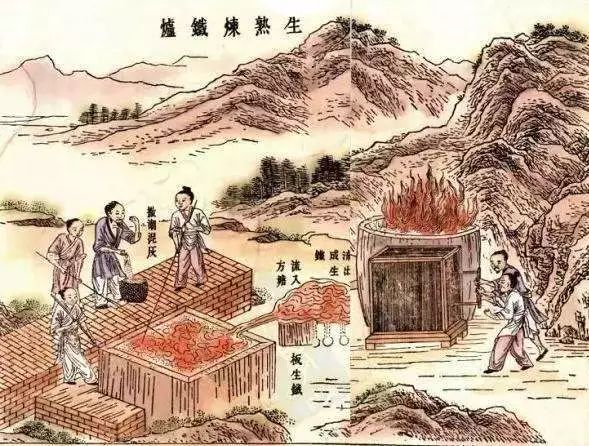
跌鼻心說,那如果你做的都是好事,那么大能耐的鬼神咋不管你,讓你好人生病呢?
面對(duì)這樣的學(xué)生,盡管很鍛煉自己的思維能力,但墨子真的很心累。
不過,關(guān)于巫馬子的身份,現(xiàn)在頗多爭(zhēng)議。有人認(rèn)為他是打入“敵人”內(nèi)部的儒門弟子,因此專門找茬,但巫馬子辯論中的主張,并不符合儒家思想,倒和楊朱的“利己”想法有些異曲同工;有人認(rèn)為,他只是《墨子》為了表達(dá)自己的觀念而憑空設(shè)置出來的一個(gè)辯論人物,以對(duì)答的方式闡述自己的理念,最后獲勝和占理的都是自己,等于“豎個(gè)靶子自己打”。如果真是如此,墨子的邏輯轉(zhuǎn)折尚且有待提高……
莊子學(xué)生委婉提問
莊子偶爾也能感受到墨子的難堪,弟子里總有些不那么省心的。
莊子的主張是避世,不太愛管塵世間的紛擾,寧可做一只在爛泥里打滾的烏龜,也不愿上朝堂被人供奉。簡(jiǎn)而言之,為了不受約束,不干996制的工作,他就只想當(dāng)個(gè)與世無爭(zhēng)的“廢物”。而“廢物”往往能得到逍遙自在。受他影響的門徒,自然也都是這一套避世和逍遙游的思想。

有一次,莊子帶弟子們?nèi)ヅ郎剑缴嚼镉龅揭蝗悍ツ竟ぴ诳硺洌欢蠹叶祭@開一棵長(zhǎng)得挺繁茂的大樹,只砍它周圍的其他樹木。莊子很奇怪,詢問緣由。
伐木工說:“這棵樹沒啥用。”類似于做家具、造船需要用什么材質(zhì)的樹,但這棵樹卻用不上。
莊子覺得此次課外的這堂課格外生動(dòng),趁機(jī)回頭對(duì)學(xué)生們?cè)俅未蚨ㄐ膭?ldquo;嘿,看到?jīng)],沒用的反而可以享受上天賦予的完整壽命。”
然后一群人繼續(xù)游山,逛到差不多天黑,莊子帶著大家下山,到一個(gè)朋友家里吃便餐。
好客的朋友見好友來了,連忙招呼家童殺只大雁招待。
家童平時(shí)喂養(yǎng)得多,對(duì)大雁的情況比較熟悉,問主人:“家里的大雁有一只會(huì)叫,有一只估摸聲帶壞了,不能叫,殺哪只呢?”
主人說:“當(dāng)然殺不能叫的那只。”
這下,莊子不說話了。在場(chǎng)的學(xué)生也陷入了沉思,沒一人發(fā)言。
第二天,有個(gè)學(xué)生實(shí)在是忍不住了,還是委婉地來問莊子:“昨天那棵樹因?yàn)闆]啥用而能活下來,后來那只大雁因?yàn)闆]用被殺……所以老師,到底我們?cè)撟鰝€(gè)有用的人,還是沒用的人?有用跟沒用,你站哪邊?”

莊子心說,好家伙,就知道有人在這等著,于是尷尬又不失禮貌地笑了笑:“有用沒用,兩邊都不行,我只能選站在中間了。”末了,又跟學(xué)生扯了一通逃離有用和無用的范疇,借我一雙翅膀,逍遙九天,做個(gè)逍遙游的人。又叮囑大家專注修德行才把話題圓過去。
儒家的杠精
莊子、墨子的問題,孔子也遇到過,而且孔門里出了位最著名的杠精,宰我。
宰我跟孔子學(xué)習(xí)以后,經(jīng)過老師的提倡,也很喜歡提問題。有一次,在孔子講孝道里的“三年守孝期”環(huán)節(jié)時(shí),宰我問道:
“三年之喪不已久乎?君子三年不為禮,禮必壞;三年不為樂,樂必崩。舊穀既沒,新穀既升,鉆燧改火,期可已矣。”
子曰:“於汝安乎?” 曰:“安。” “汝安則為之。君子居喪,食旨不甘,聞樂不樂,故弗為也。” 宰我出,子曰:“予之不仁也!子生三年,然后免于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,天下之通喪也,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!”
大致意思是,宰我說:守孝三年也太久了,而且老師你不是提倡我們?nèi)粘I疃家鸲Y、守禮嗎?如果三年就干守孝這一件事,而不搞搞禮樂,那禮也壞了,樂也崩了。依我看,一年就夠了,一年時(shí)間,咱們?nèi)ツ甑募Z食也吃完了,新的糧食也該播種了,不耽誤事。

孔子說:就守一年你心安嗎?
宰我:我心安啊。(這句顯然有杠上的性質(zhì)了)
孔子(╮(╯▽╰)╭):你心安就行,你開心了好了。
宰我出去以后,孔子嘮叨:宰我真不仁啊,孩子出生后三年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獨(dú)立行走,守孝三年他都做不到,難道宰我對(duì)父母連最后三年的愛都沒有嗎?
其實(shí),宰我是從實(shí)用主義出發(fā)考慮,畢竟不能因?yàn)閱识Y耽誤農(nóng)事。孔子則還是從人性的角度審視宰我,而沒有正面回答問題,事實(shí)上,古代的守孝三年,不是滿打滿算三年整,而是兩年零一個(gè)月,就算第三年。而守孝的過程正是“禮”的行為準(zhǔn)則之一,“禮”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