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:擇一青花小盤盞,一白瓷小搗杵,香臺一旁的茶缶里橄欖碳火紅,鐵壺里山泉略沸香案上的宣德爐,宿火常熱,色如秋梨,細(xì)撥活灰一寸,灰上隔砂選香以蒸,其香滋潤而幽甜。“有點感覺,現(xiàn)在可以做香了。”回味著建窯兔亳盞里金駿眉的后味,沈才松笑著說。
擇一青花小盤盞,一白瓷小搗杵,香臺一旁的茶缶里橄欖碳火紅,鐵壺里山泉略沸香案上的宣德爐,宿火常熱,色如秋梨,細(xì)撥活灰一寸,灰上隔砂選香以蒸,其香滋潤而幽甜。“有點感覺,現(xiàn)在可以做香了。”回味著建窯兔亳盞里金駿眉的后味,沈才松笑著說。

爐火純青

離蘇州博物館不遠(yuǎn),水巷子和石橋漸漸多起來了,白墻黑瓦的小院落也多了,有些老蘇州的味道了。36歲的鄭育樹的工作室在七扭八拐的巷子里,事實上,那也不過是和別人合租的一個倉庫,鄭育樹顯然很滿足現(xiàn)在的狀態(tài),“比以前可好得多啦,那時候才4個平方,停車庫改的,轉(zhuǎn)個身都麻煩。”他笑著說。這個16歲開始做白鐵匠的中年人目前靠做手工香薰?fàn)t為生,每日里,煙云入懷,暗香盈袖。從白鐵水桶、水吊子、通風(fēng)管道直至“沉香斷續(xù)玉爐寒”,世俗與風(fēng)雅或也僅在一念之間。
600年前的蘇州是“紅塵中一二等的富貴風(fēng)流之地”,諸般風(fēng)雅韻事在物質(zhì)文明高度發(fā)達(dá)的江南蔓延開來,以“點茶、焚香、掛畫、插花”四般閑事為主流的士大夫修養(yǎng)流行在老蘇州城的每一個園子里。士族文人津津樂道于水木清華,室廬清靚,追求生活細(xì)節(jié)的高度藝術(shù)化、精致化。他們親自參與設(shè)計園林、水石、家具、文玩,而香薰更是坐而論道、燕閑清賞不可或缺的雅物,夜雨篷窗,摩挲把玩,金玉青煙里,或有助遐思。
眼下,鄭育樹的思緒都在裁剪好了的紫銅皮上,噴槍的淡藍(lán)色火焰均勻地將材料加熱到適合鍛打的溫度,能借助的工具也是簡陋的,一把加長的鐵圓規(guī),幾把小榔頭,鑄鐵的模具,若干銼刀幾乎就是全部的家當(dāng)了。趁著銅皮的熾熱,小榔頭叮叮咚咚地敲起來了,圓形的銅片規(guī)規(guī)矩矩地在模具里敲打成型。“紫銅色澤漂亮,延展性好,比黃銅軟,打造起來也省力些。”鄭育樹說。憑著當(dāng)年跟蘇州制香爐大師陳巧生學(xué)得的手藝,鄭育樹對于香薰的手工制作已然駕輕就熟。
他制作的香薰并不采用當(dāng)下流行的失蠟法工藝,而是傳統(tǒng)的,費(fèi)時費(fèi)力的銅板焊接法,“專門拜師傅去學(xué)了電氣焊,考了個證出來。”他靦腆地說。看似簡潔的銅香薰要經(jīng)過開料、退火、敲接成型、焊接、整形、打磨、后期整形、上色等多道工序。一張紫銅皮,在他的手里變幻著不同樣式和紋理,爐出其手,古韻盎然,形色俱佳。唯吾知足爐有大象無形之簡,回紋四足大臥香薰的凝重沉穩(wěn),雪香云尉壽字篆香爐的雅致雋永,五福捧壽三足熏爐的古樸大氣,比古時名匠之手,亦不遜色。
工藝較為復(fù)雜的雙層朝冠耳熏爐由57個銅件焊接組合而成,“一個簡單的熏爐蓋子,也需要至少5個部件配起來,最簡單的’口筋’都不能馬虎,否則這個香薰就走樣了。”盡管在拍攝中穿插的采訪,也絲毫沒影響到他的專注,手里的小銼刀正仔細(xì)地磨去香薰蓋子上的毛刺,鏤空雕的圓蓋飾著曼妙的纏枝紋,銅色如蒸栗,溫潤中令人遙想暗香浮動,人影黃昏。
紅袖添香

如若不知底細(xì),走進(jìn)沈才松的會所,會以為貿(mào)然闖進(jìn)了一個中藥鋪子,青花小梅瓶和金絲楠木的小抽盒里游絲般的香氣迷離在空氣里,若有若無,若即若離。檀香、梅花腦、沉香、香附子、百合根、蕓香、木樨、豆蔻、奇楠、冰片……精致的小楷標(biāo)注出了合香所用的諸多元素,它們采自不同的地域,卻都是造化之精華,草木熏隆,梅英半舒,香丸尚未做得,人倒在微醺中醉了半分。
擇一青花小盤盞,一白瓷小搗杵,香臺一旁的茶缶里橄欖碳火紅,鐵壺里山泉略沸香案上的宣德爐,宿火常熱,色如秋梨,細(xì)撥活灰一寸,灰上隔砂選香以蒸,其香滋潤而幽甜。“有點感覺,現(xiàn)在可以做香了。”回味著建窯兔亳盞里金駿眉的后味,沈才松笑著說。然后,瓶瓶罐罐們集中在了影木香盤里,看上去琳瑯滿目、熱熱鬧鬧,真還有些古時藥號的意思。“天冷了,我們做一些暖香丸吧。”他說。窗外臘悔正盛,軒窗微掩,亦難抵冷香盈袖,屋內(nèi)則圍爐品茗,瑞腦銷金獸,頗合時宜氛圍。
檀香和丁香是暖香丸的主材,偏甜的香型更適合嚴(yán)冬季節(jié)。“香丸也要講究個陰陽調(diào)和,不能燥,所以要加些沉香和冰片來中和一下,但用量就要比夏天的冷香丸少得多啦。”沈才松邊拾掇香材邊說。
檀香有和胃之力,丁香香甜,可增香氣中的花香意味,冰片為濃香,多則膩,少量加之,能去檀香中的燥熱之氣,沉香可融合各種香材,確定香丸的基本格調(diào)。煉蜜和炭屑也是香丸中不可或缺的東西,煉蜜是將普通蜂蜜隔水而蒸,再與炭火中去掉水汽,而后放置地底存儲起來,如此,方可只留蜜之甜香而雜味盡除。
研磨香材也是項精細(xì)活兒,“比如做線香吧,你就要打磨得很細(xì)膩,像店里賣的精面粉一樣最好,否則就會斷掉。做香丸就可以略粗一點,比芝麻略細(xì)就可以用了,這樣熏香的時候香氣會更持久一些,如果是做香囊,則更粗一些,甚至不用怎么打磨都可以。”沈才松用銀勺取了不同的香材,仔細(xì)稱量后,放進(jìn)青花盤盞里,開始研磨起來。不同的香材有不同的脾性,用香材的比例要看彼此的香型是“沖”還是“合”,是隱香還是濃香,如冰片就是特濃的香材,量多則極膩,而桂花則屬隱香,多置亦無不可。似中藥配方一般,講究君臣輔佐,遵從君香臣香,與傳統(tǒng)中醫(yī)藥理頗有相通之處。
香材和炭屑充分研磨成末后就可以加入煉蜜搓制香丸了,充分融合后的各種香材要揉透。“這個道理就像是廣東潮汕—帶著名的牛肉丸子,要打透打均勻了才好。
古時候,合了香,還要在地底下埋上十幾天或一個月,讓各種香料的味道再次完全融合,現(xiàn)在做好的香丸,總還得陰干幾天才能派上用場,今天急著獻(xiàn)香,就拿上次做好的暖香丸吧。”沈才松手里的云雷紋剔紅香盒里,擺著灰黑色的五六粒香丸。仿官窯如意紋三足爐里,炭火早已溫?zé)幔孟銑A取出一枚香丸,輕置于爐中炭火之上的云母片,蓋上純銀鍛制的編織紋爐蓋。片刻,即有芳馥,暖而甜糯,綿長中夾雜著冰片的清涼,絲絲人心。傳爐而品之,頗有曲水流觴之雅。屋外暖陽已斜,紫竹婆娑,友人取琴操縵,竟是《普庵咒》,恍惚間,卻也不辨香與禪了。
品香問遭

敬廬主人在自己的會所里為選一款合適的香爐而糾結(jié),可選擇古董香具太多,難免在取舍間躑躅。而賞器、品香與傳統(tǒng)的香道而言,幾乎同等重要。一座色近棠梨,凝重壓手的清早期蚰龍耳宣德爐最終勝出。爐經(jīng)數(shù)代主人常年溫火慢養(yǎng),巾裹帕圍,初鑄時的火氣早已褪盡,唯爐底“大明宣德年制”六字楷書款識依舊刀鋒犀利,靜中晤對,競忽欲浮動。古銅爐瓶作梅瓶式,色如液金粟玉。置純銀香具若干,香匙、香夾、探針、頂花、灰鏟……銅鎏金香盒為清代官作,斑駁中透出時間歷練出的的溫潤。紫檀文盤以上等云石為底,取天成之紋理,若峰巒疊嶂,有溪山行旅之意。
香具俱備,香事則獨缺香材,香之最優(yōu)者,伽南止矣。以購之甚艱,非尋常山家所能卒辦。其次莫若沉香。沉有三等,上者氣太厚,反而嫌于辣;下者質(zhì)太枯,而又涉于煙;惟中者約六七分一兩,最滋潤而幽甜,可稱妙品。敬廬主人于柜中取珍藏之綠棋楠,謂之“鶯歌綠”。
置于黃花梨香盤中,其形如枯木,而紋似鶯羽,香力幽甜且溫潤。爐內(nèi)香灰為宣紙與松針精細(xì)煅燒而成,色純白而絕無他味。取香炭一粒,埋入香灰中,以火引之,燃至炭色灰白,方可盡除煙火氣,與品香無擾。復(fù)以香灰蓋之,以探針與灰堆上開一小孔,以保炭火持久。
香押將松散的爐灰塵壓緊并形成簡潔凝重的紋理,待用羽掃輕輕將浮灰掃清,敬廬主人這才順著香材的紋理,仔細(xì)切下一小片,置于純金葉子,取入爐中,徐而燕之。但見一香凝然,不焦不竭,郁勃氤氳。五代的羅隱有一首詩寫道:“沉水良材食柏珍,博山爐暖玉樓春。憐君亦是無端物,貪作馨香忘卻身。”
接過敬廬主人雙手奉上的香爐,頗有些忐忑,生怕辜負(fù)了這極珍貴的香材。一手握爐,一手虛掩于爐上,距鼻翼三寸余,初時幾不聞,只覺手中的溫?zé)崤c鼻息中的游絲般的香意。待撲蝶般地捕到一縷,早已如蜜露滑入心扉。再片刻,那香宛若蓮瓣,隨風(fēng)落波,緩緩地漾開了去,甜暖間有不易察覺的清涼,漸至物我兩忘,儼居太清宮與上真游,自有不可形容之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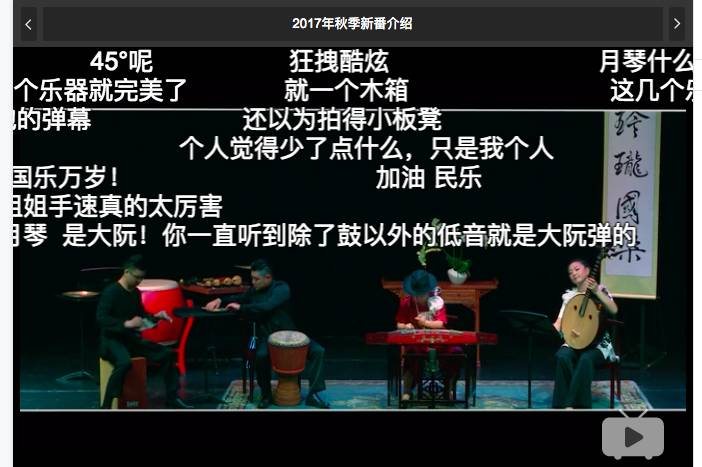
- 下一篇: 唐朝人過年的姿態(tài)
- 上一篇: 中國人何時開始穿褲子?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