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:我們常說,若比喻一個女子傾國傾城,莫過于拜倒在其石榴裙下。石榴和裙子的形象從小就莫名其妙被捆綁,而且和女人有關(guān)。若有聯(lián)系,第一感想便是石榴啊,養(yǎng)顏啊美容啊,最主要是解餓——一到晚上腦子里首先閃現(xiàn)了這個。

我們常說,若比喻一個女子傾國傾城,莫過于拜倒在其石榴裙下。石榴和裙子的形象從小就莫名其妙被捆綁,而且和女人有關(guān)。若有聯(lián)系,第一感想便是石榴啊,養(yǎng)顏啊美容啊,最主要是解餓——一到晚上腦子里首先閃現(xiàn)了這個。

一句石榴裙不僅代表女子的氣質(zhì)非凡,而在于古人對正色的喜愛早就體現(xiàn)出來了,孔子曾說“紅紫不以為褻服”,即不能用正紅色或者正紫色的布做家居時的便服。《詩經(jīng)·七月》中“我朱孔揚,為公子裳”突顯了紅色的高貴,以證明當(dāng)時染紅的朱砂取得不易。后世紅色染料則多為植物染料,孔子所說的紅,其實指的便是正紅朱色,也是最接近石榴的顏色。為什么說這種顏色尊貴?有小部分原因則是染色難度之大,用料之費。石榴可用來染色,但古代還是普遍以茹藘,即茜草染材而成紅,由深至淺,大致有朱、赤、韎、璊四種層次。茜草一入為最淺的紅,叫韎;再入為璊,為稍深的紅;繼續(xù)染色為赤,近紅;反復(fù)染色才為朱,耀眼、尊貴的紅,即我們所認(rèn)為飽和度極高的正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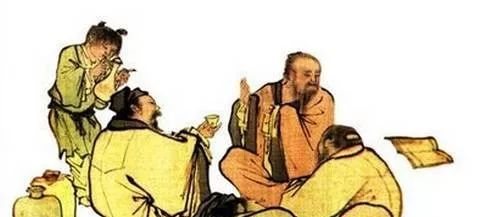
再說到石榴裙的“石榴”二字。據(jù)傳張騫出使西域,才帶回石榴,因物以稀為貴,難以買到,價格也是出奇,《洛陽伽藍(lán)記》中即有“白馬甜榴,一實值牛”之說。以石榴一名來稱呼裙子,則顯示了一條裙子的魅力。雖說石榴裙以其他如茜草等植入染色,但當(dāng)時能擁有石榴裙的也大多是家庭擁有一定經(jīng)濟實力的女子,后來直到女子人手一條,也足以見得其流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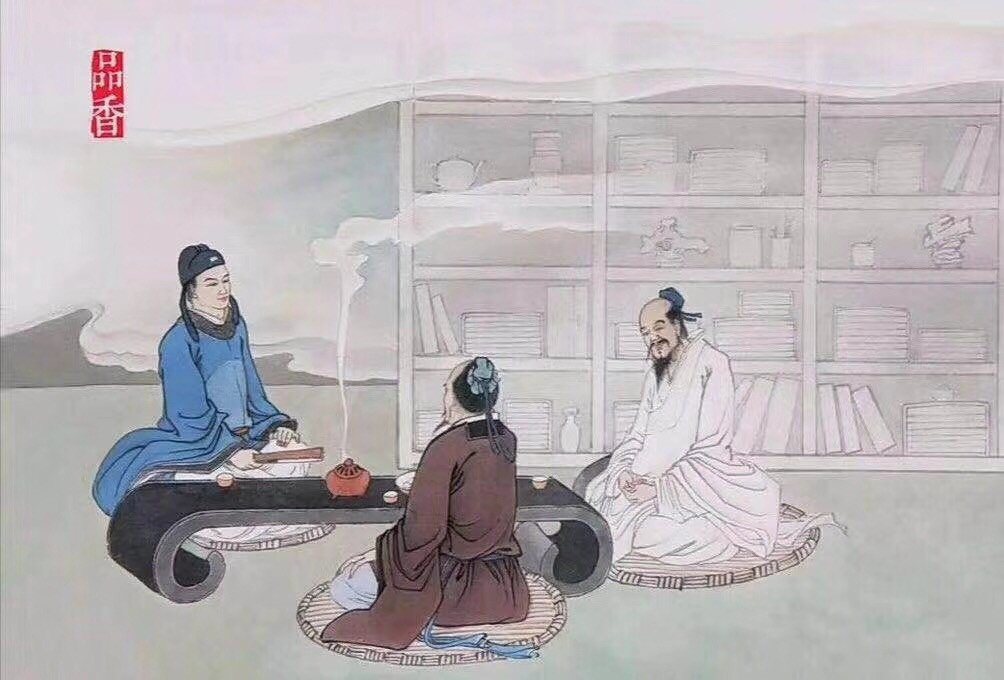
既然石榴裙和石榴并無相關(guān),那為什么叫石榴裙?前面講到了紅色的來源和石榴一詞的“貴氣”。而唐代的女子,就喜歡穿這種顏色的裙子,其色如石榴之紅,故稱為石榴裙。再后來石榴裙三字在文人墨客筆下也逐漸成為了女子的代名詞,現(xiàn)代人都知道,穿上正紅衣服,膚色顯白,氣色顯好,而在遙遠(yuǎn)的唐代,顏色未必如現(xiàn)在工業(yè)染色之純,卻也因穿上了石榴裙,而顯得明艷動人。梅花香滿石榴裙。風(fēng)卷葡萄帶,日照石榴裙…寫的是花,明明是美人。這一句句詩文中的石榴裙,讓人想起唐詩宋詞里的燈火闌珊,想起不同節(jié)慶的繁華鬧市,想起草長鶯飛的江南春色,讀起來,竟是滿口香甜。

長裙與女子,也成了古文化中一抹不可縮寫的倩影。而月涼如水的夜里,也會想起這樣平淡的句子,自此長裙當(dāng)壚笑,為君洗手做羹湯。若說男子為女子肯拜倒其石榴裙下,是一種折服,而女子愿為男子拋下榮華,甘當(dāng)洗衣廚娘,那便是另一種由心而發(fā)的境界與生活了。總歸,無論怎樣的選擇,都有每個女人、自己動人的理由。



